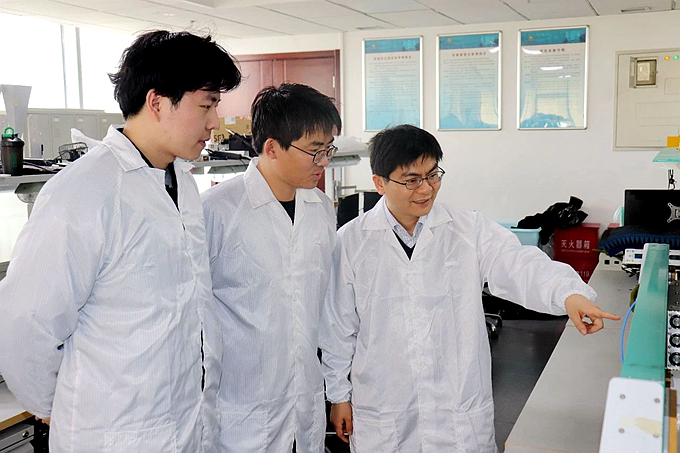【校報】《現代圣人徐特立》之開創先河
發布日期:2010-07-10 閱讀次數:
來源:《北京理工大學校報》第770期、771期第4版 編輯:黨委宣傳部 國慶
《北京理工大學校報》第770期鏈接:http://xiaobao.bit.edu.cn/media/user/2010-06-21/show2.html
《北京理工大學校報》第771期鏈接:http://xiaobao.bit.edu.cn/media/user/2010-07-05/show2.html
《北京理工大學校報》第770期鏈接:http://xiaobao.bit.edu.cn/media/user/2010-06-21/show2.html
《北京理工大學校報》第771期鏈接:http://xiaobao.bit.edu.cn/media/user/2010-07-05/show2.html
【編者的話】值此學校70華誕即將來臨之際,我們特別懷念為學校建設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先輩們,特別懷念北京理工大學精神風骨的重要締造者之一徐特立老院長。《現代圣人徐特立》(師秋朗著,紅旗出版社,1992年10月北京第1版)一書記載了徐老光輝的一生,濃墨重彩地描述了徐老擔任自然科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院長期間的經歷。校報自本期起將陸續刊登此書相關內容,以紀念徐老為中國革命事業、教育事業和自然科學院建設發展做出的豐功偉績,以鼓勵師生重溫歷史、牢記教誨、見賢思齊、激情進取、再創佳績!
1940年8月12日,徐老一行到達延安。13日,正是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三科(即各縣、區的教育科)科長會議開幕,徐老不顧長途跋涉勞累,趕去參加會議,并致詞。與會者受到極大鼓舞。會間,他又做了《各科教學法》的專題報告,使與會者滿載而歸。
從此,徐老穿梭于學校、學術團體和工廠之間。擔任教育學會會長等職。在對各方面工作的指導中,格外重視自然科學的教育和研究。他為兩年制師范教育親自起草了自然課程標準和教材大綱。當時延安已集中了一批科技人才,成立了自然科學研究院,不久又改為自然科學院,招收學生。徐老寫了《怎樣進行自然科學的研究》一文,載于《中國文化》1940年第二卷第四期。該文首先提出科學的任務:“就總的方面來說,我們的科學應該替抗戰建國服務。無論是一般的研究,專門的研究,理論的研究和技術的研究,其總的任務只有一個:即在物質上加強和擴大我們的抗戰建國力量。”“一切科學都是建筑在產業發展的基礎上,科學替生產服務,同時生產又幫助了科學正常的發展。”“科學替抗戰建國服務并不是縮小科學的范圍,也不是降低研究的程度,相反的,而是加強理論的物質基礎和加強技術的理論指導,同時把理論和技術在生產上和大眾聯系起來,在研究自然科學時,同時研究生產方法和方式。”“科學從生產出發,一方面加強了我們的國力,另一方面又幫助了科學自身的發展。”
關于“研究科學的方式”,他從當時物質條件“驚人的缺乏”這一現實出發,提出了一系列充分利用圖書資料和儀器的措施。關于“科學研究的方法”,他認為從蘇聯的經驗和邊區的實際論證了理論聯系實際是基本的方法。最后寫道:“科學每一日都在發展中,科學的研究方法同樣不是固定的,現在提出的只是開步走的問題,前面的行程還需要隨時找向導。”
年終時,徐老被任命為自然科學院院長。
1938 年—1939 年,從國民黨地區先后到達延安的高級、中級知識分子有了一定的數量,為發揮他們的作用,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學研究院,附屬于邊區銀行。
鑒于蘇聯十月革命以后由于缺乏自己的科技人才而吃了大虧的教訓;為了全國勝利后經濟建設的需要,必須培養自己的科技人才。于是中央決定在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的基礎上,培養學生,成立自然科學院。
自然科學院籌建過程中的院長,是由當時中央組織部部長并管財經的李富春兼任。在當時的條件下,籌建一所自然科學的大學,談何容易!
宋慶齡為抗戰而吸收華僑和國際友人的人力、物力、財力,創辦了中外聞名的工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工合對延安的教育事業和工業建設,給予了大力支援。著名國際友人路易·艾黎(1988 年逝世于北京)以工合的名義數次到延安。她的母親仍在本國新西蘭,卻以自己1 萬美元的養老金捐獻給自然科學院,作為籌辦經費。80 歲的老太太還騎上自行車到處奔忙,為中國的抗戰募捐。
周恩來在重慶也盡力為自然科學院搜集書籍器材,但很難帶進邊區。
有些科技人員冒著生命危險到國統區的大城市去購買器材,劉公誠(現國家建設部)、聶春榮(中國科協)、陳寶誠(已故)等不避艱險采購過器材。有的獻出了生命,如王克、吳志超在西安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自然科學院辦起來了,學生也到了,正好徐老回到延安,接替了李富春任院長。教學秩序迅速建立起來了。陳康白和自己敬重的老師共事,格外高興。此外還有留德博士屈伯川任教務長(現大連工學院名譽院長),以及一大批在大學任過教和大學畢業的一批人成為教學骨干。
學生大體分三部分:大學部,人數不多,四個系(化學、物理、地礦、生物),每系只有學員五六名,系從國統區來的高中畢業和大學未畢業的學生;預科兩班60 余人,系從國統區來的初中畢業生和高中生,他們經過基礎課的充實之后即可升入大學;還有數百人的補習班,相當于初中,成分主要是邊區自己培養的小學畢業生,工作崗位上相當水平的少年,也有部分從國統區來的青少年。其中有較多的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還有一個醫訓班,白求恩醫科大學成立以后這個班并入了醫大。
交代這些背景,因為和當時的爭論有關,和徐老的見解有關。
到1940 年,我們年輕的黨經歷艱苦卓絕的斗爭,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下,都重視教育,中等、高等學校辦過不少,但基本都是培養軍事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辦自然科學院,卻是破天荒頭一次,也算新事物吧。尤其是中國歷來只有富家子弟才能上大學,無產階級也要掌握自然科學,許多人,包括工農干部一時也認識不到必要性;而當前要緊的是抗日,是打仗,那些ABC 什么時候用的上?這是當時一部分干部中的看法,認為遠水解不了近渴。甚至一位相當負責的干部,認為杜甫川(自然科學院院址)那么優美,辦個干部療養院也比辦自然科學院強, 于是請徐老吃飯,想得到徐老的配合,徐老謝絕了“美意”,他方知徐老不會讓步。
另一些不同看法,發生在知識分子中間。在生產部門工作的干部,認為沒有必要從中學開始培養科技人才,不如把這些中小學畢業生送到工廠當學徒,就能很快發揮作用,現有的大學教授、教師等都應該到生產部門去發揮作用;另一種意見認為大學是要辦的,但只有像大后方(國統區)那樣的大學才是大學,我們卻不具備那些條件。前一種認為不必辦,后一種要辦又辦不了,結局一樣,都是不辦。
徐老一方面和人們廣泛交談,聽取意見,溝通思想,一方面堅持辦好自然科學院。
在他的倡導下,1940 年2月自然科學院研究會成立,并發表了宣言,宣言中 寫道:“開展自然科學大眾化運動,進行自然科學教育,推廣自然科學知識,使自然科學能廣泛地深入群眾……”,“集中自然科學界同志,互相交換意見,共同解 決自然科學理論和應用上的問題……, 推進生產事業協助經濟建設……”,“運用唯物主義辯證法來研究自然科學,并運用自然科學來證明與充實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理論。”到了1941年,地質學會、 醫藥學會、生物學會、機電學會、化學學會、數理學會等相繼成立。舉行年會、發表論文、考察、展覽、觀察日蝕等活動很多,《解放日報》也不乏報道,科技人員情緒高漲。
由于人才集中,自然科學院的教師除了完成教學任務,還為邊區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例如:陜甘寧邊區書、報的印刷量很大,可是紙張奇缺。教員華壽俊 (現中國科學院西安分院副院長)研究成功用馬蘭草造紙,馬蘭草是陜北滿山遍 野的野生植物,用它造紙并無先例,試驗成功,當即投入生產,解決了邊區的用紙。關系到邊區經濟命脈的鹽,因連續大雨,鹽池產不出鹽來,華壽俊、陳康白、陳寶誠到了定邊,實地考察,并向鹽民調查研究,終于找到了簡便易行的好辦法,不僅產量穩定提高,而且所產的鹽基本是精鹽。華壽俊回延安向中央匯報時,到安塞振華造紙廠遇到了朱德總司令,朱德知道他發明馬蘭草造紙之后又取得了新的成果,很是高興,隨即在華壽俊的筆記本里寫下了“我們的發明家”幾個字。邊區的玻璃制品奇缺,搞科學實驗要用玻璃試管、燒杯,三角瓶等,醫院也用這些器皿,晚間照明用的煤油燈,沒有燈罩,光冒黑煙,等等。為解決這些急需,本是油類工業專家的林華(國家計委副主任) 教員承擔了試制玻璃的任務,在缺乏參考書、缺乏原材料、缺乏技術工人的條件下,他跑了多少溝,翻了多少山,找到了原材料,經過克服種種困難,終于試制成功。后來劉威一(西北工學院原院長,己故)任玻璃廠廠長。《解放日報》以《模范工程師林華同志》為題,報道了他的事跡。華壽俊和王士珍(女,華壽俊的愛人、 西安光機研究所所長)還從野生植物和黑豆皮中提取染料成功,可制出醬紅、青 灰、咖啡色、綠色、血青、元青、青灰、墨綠 等色。解決棉布困難,李丹(中國情報所 重慶分所所長)、華壽俊、王士珍共同研究用邊區產量甚豐的麻提取麻纖維制成麻棉布。朱德提出需要一塊既可練兵,又能生產的場所,生物教員樂天宇(已故) 等同志在考察陜北植被時,發現了南泥灣,向中央報告被采納,南泥灣從此出了名。陜北很少有鐘表,個別帶手表的人, 時間不準了也無法對正,青年教員江天成(原國家建委化工輕工局局長)為幾個大單位制作了日晷,只要有太陽,一年四季都是十分準確的。其它諸如幫助建立火柴廠、日用化工廠,考察植物、礦藏等 弄清家底,制作標本,開展覽會,科普教 育等等,一時也說不盡。
盡管自然科院為邊區做了那么大的貢獻,解決了那么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似乎人們原來怎么想,還是怎么想。
最不愛寫文章的徐老,1941年9 月,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 《怎樣發展我們的自然科學》。文章一開頭就寫道:
前進的國家與前進的政黨對于自然科學不應該任其自發的盲目發展,而是有計劃有步驟的發展。它不僅應該把握著全國的政治方針,還應該把握著全國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方針。
他在分析了全國(包括國統區和邊 區)的科技事業和教育的狀況后寫道:
先進的政黨,每一步驟都不會忽略 過去的歷史,同時每一步驟,都照顧著將來。見近不見遠,只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中的實利主義者,見遠不見近,只是小資 產階級的烏托邦主義者。抓住中心的一環,又照顧到鎖鏈的全面,就必須有周密的計劃和詳細的調查,反之,如果粗枝大葉而為之,與枝枝節節而為之,沒有整個發展科學的計劃,科學的前途是暗淡的,同時也是先進政黨的一個最大的缺陷。
在說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自然科學,以及科學家如何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之后,又說:
科學家還應該照顧到實際條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沒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礎,幻想提高科學是不可能的。如果當抗戰開始時,在邊區即提出學校正規化,不需要軍事和政治的訓練班,是非實際的。 如果當沒有小學生的時候而提出建立自然科學院也是非實際的。但是有了起碼的條件只等待著條件完全具備,而不愿在已有條件下加以創造,只知道天定勝人而不知道還有人定勝天,同樣是錯誤的。可以說,空想主義和實利主義對于科學建設同樣是有害的。
李維漢同志在《群有師尊黨有光———懷念徐特立老師》一文中說:“徐老“力排眾議,堅持把自然科學院辦下去”,在這里可見一斑。
徐老在這篇文章的最后說:“原則上的爭論,應該發展,因為只有爭論才會有新的理論產生出來。”而當時“……這些問題,性質既復雜又無專門機關來解決,于是只有爭論,沒有結論,因而影響科學界的負責人舉棋不定。對于科學的一切建設,在某些部門旋定旋廢,在無原則的變更下,一方面促進科學的前進,另一方面又引起它的后退。我希望科學界發展爭論,在理論上不做最后的結論,但實際工作必須做出正確的結論,以便有規律地進行工作。”(未完待續)
(本文轉載自《現代圣人徐特立》,師秋朗著,紅旗出版社,1992年10月北京第1版。)